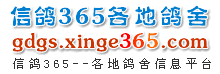春节过后,北京的白天最高气温保持在零度上下,人们还穿着厚厚的冬衣,但天赋灵性的信鸽似乎已经听到了春姑娘轻盈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分居日久的雄鸽和雌鸽,神情变得兴奋,叫声欢快而响亮,它们的春心萌动了!
每一位鸽友都在谋划,今春如何给种鸽组对呢?我的心中也在暗中思忖:能不能搞一次试验,把择偶权交给种鸽自己,而不搞人为的自以为是的所谓指定配对!
多少年来,信鸽的择偶问题多是由其主人“包办”。因为信鸽界有流传多年的“配对经验”,诸如:黄眼配砂眼、体型大配小、赛绩鸽互配、眼志宽配窄、不同血统鸽杂交配等等,不一而足。
我近年因无暇顾及鸽会比赛,以打公棚为唯一的参赛模式,每年送出40-50羽幼鸽至公棚,就像“刀耕火种”时代的原始老农民,春天播种下去,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秋天的收获如何,全凭老天爷的心情了。而种鸽的婚配问题,自然是沿袭鸽界习俗——由我包办。几年比赛下来,总是有胜有败,自己认为很理想的种鸽配对,并没有作出公棚获奖鸽。而自己并不倚重、不寄厚望的种鸽配对却能作出不错的公棚赛绩鸽。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促使我不得不反思鸽主在种鸽择偶问题上的“经验”,到底有几多指导意义?那些流传于鸽友口头上的或是见诸于各种信鸽媒体上的“理论”或“经验”,毕竟是来自于一棚一舍的一两个种群,或许也是“偶然”的产物,而鸽友却错把这偶然的成功当成了必然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成功的个案也应当归属于“歪打正着”。因为鸽子身上有太多的、未被揭示出来的“谜”。
既然包办的“指定配对”与“并不倚重、不寄厚望”的试验性配对在作出效果上不相上下,而且均与鸽主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们又何必绞尽脑汁、主观片面地去琢磨所谓的“指定配对”呢?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让我们的思维从“人为环境”跳到“野生环境”。猴群中有“猴王”,狼群中有“头狼”,那这“猴王”和“头狼”的父母的婚配是由谁指定的?再进一步说,“猴王”和“头狼”的同胞兄弟是否也是“猴王”和“头狼”?“猴王”和“头狼”的儿子,是否还能当种群中的首领?把这个问题移到信鸽育种上:一对种鸽繁育出了冠军鸽,那么,这对组合再次作出冠军鸽的几率有几何?冠军鸽的子女又有几羽能“世袭”冠军?有人认为:自然界中,一切动物的遗传都充满了变数、充满了“随机性”,少有或根本就没有规律可言。我赞同这个观点。多年以来,我始终记着赵忠祥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电视片中的一句解说词:“种是强者的延续”。我认为,猴王、头狼、 冠军鸽都诞生于它们父母的一次偶然的交合,使它们获得了强健的体魄、凶猛残忍的性格或聪慧的头脑。这偶然的交合,造就了它们成为“王者”的必然,因为它们比同类强健、凶残、聪慧。鸽友们常说:冠军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句话其实也从侧面揭示了信鸽遗传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鸽友们不断地引进更为优秀的种鸽,选择更为完美的种鸽组对作育,充其量只能是极为有限地提高作出优秀赛鸽的机率,想彻底改变信鸽育种中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与其如此,我们不如尝试一下,把种鸽的“择偶权”交还给种鸽自己。让它们根据自己的择偶标准,以及情感上的要求去自由恋爱和婚配吧。我相信,信鸽是有情感的,也有它们自己的交流方式,正如古人所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
在主张信鸽自由择偶的同时,鸽主也可以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比如,鸽主要保证进入种鸽舍的雄鸽和雌鸽均是具有优秀竞翔素质的种鸽,还有就是在育种前的健康整理以及优质种鸽饲料的提供等等。
说是任由种鸽自由择偶,但这自由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我们要培育的是赛鸽,人的意志、通过比赛而进行的存优汰劣,都要由人来完成。
春节过后,当我把雌鸽们陆续捉入雄鸽棚时,雄鸽棚沸腾了!它们响亮地鸣叫着、追逐着,这也许就是一曲欢快的“鸽语大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
细观棚内的婚配情况大致如下:
一、曾是夫妻,并且恪守曾经的“海誓山盟”的,自然是久别胜新婚,百般温存与缠绵。
二、也有“陈世美”式的“悔婚男儿”,置原配雌鸽于不顾,将“新欢”金屋藏娇。
三、精神虽然亢奋,但并不急于婚配,在棚内游弋巡视、鸣叫,似乎对棚内现有的雌鸽不满意,也许在期待着主人把更多的雌鸽放进来,以便它们在更大的范围内“海选”。
四、确实有忠贞不二的雄鸽,因为它们去年的配对雌鸽已经不在了,虽然新放进种鸽棚的年青雌鸽足够多,但它们不为其所动,只是伏在巢箱门口“呜呜”地长鸣不止,无疑是在呼唤昔日的情侣,它们分明在演唱另一首歌曲——《我的心在等待》。
任它们去吧,把自由最大限度地交给你们,看你们秋后给我交出一张怎样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