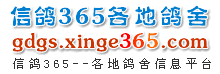注:本文刊登在《信鸽365》杂志 2013年第四期,转载请注明!
蓝天主人
达尔文的生平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R.Darwin)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其实先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英国,都相信上帝的主宰、相信上帝创造一切是对每一个人的道德束缚和思维束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受人尊重的医生,他们以这个职业为自豪,所以也就希望达尔文将来继承祖业,于是1825年他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然而事与愿违,达尔文并没有按照他父亲规划和期盼的轨迹发展。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后,他无意学医,仍然喜爱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严谨而守旧的父亲虽然认为他这是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因而十分恼怒,但仍然继续“给予正确的引导”—— 于1828年又将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
凭心而论,达尔文的父亲算是一个称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他把达尔文送到剑桥大学是一种呕心沥血的变通,既不违背自己的原则又照顾了达尔文了爱好和情绪,人情味十足。不过达尔文没有理会这些,他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正规训练,坚定地走了一条通向科学与真理的道路。1859年,他出版了震惊那个时代并影响至今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
谈达尔文的生平和《物种起源》必须要提到他的婚姻。或许是预想到可能对自己今后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达尔文对婚姻大事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谨慎的必要性。据说,当时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通过证明认为结婚的好处大于单身的好处,所以得出结论“必须结婚”。
青梅竹马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比达尔文大一岁,她冰雪聪明,心地善良,正是达尔文心仪的那种贤妻良母型女子。他们两情相悦,双方家人也倾力撮合。水到渠成结婚之后,他们拥有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这段看起来十分圆满的婚姻却有一丝隐患,即信仰不同。达尔文是无神论者,而爱玛是个基督徒。她很爱达尔文,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而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不过她没有要求丈夫过多,只是希望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
他们共同深爱的女儿安妮的去世是这个家庭里的一次重要事件。就是在那种背景下,爱玛的心中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认为女儿安妮的病故是上天对自己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这样“不道德”行为的惩罚。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这里我们在被达尔文和爱玛的故事感动的同时,欣慰地看到了爱情的力量战胜了信仰的差异。
爱玛是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的一个代表,她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因为她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甚至她可能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她只是爱自己的丈夫,所以给他改改手稿中的错别字或者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
假如达尔文在当初婚姻证明时,不结婚那栏里理由再多些;假如他继续呆在伦敦知识分子中间保持单身;假如他真没有和爱玛成家,那么他很可能写出一本更为激烈的《物种起源》。由于爱玛的参与,达尔文或多或少没有能摆脱感情的羁绊,从而影响了事实分析和逻辑推理。当然,我们没有一点权利去指责这样一个善良伟大的女性,在她的立场上,她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已经是够包容、够支持的了。改变人类文明进程这样重大的使命,怎么能够由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呢?爱玛负不起这个责任,也不应该负这个责任。
《物种起源》成书十几年后,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但是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或许那只是善良的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支持而杜撰的一个美丽的故事。
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那么,在他一生中到底对信鸽做过哪些研究呢?敬请广大读者关注《关于达尔文对信鸽研究的研究》的第二集。
第一章 信鸽的首要特征
达尔文自己养了很久的鸽子,而且很爱鸽子,只是他没有像今天我们鸽友那样去赛鸽。由于年代和地域的差异,关于达尔文养鸽的具体情况,作者掌握的一手材料几乎没有,就是二手材料也少之又少。记得少年时看过一部描写达尔文生平的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他和鸽子亲密接触的场面。这一细节提醒我们:这位科学巨匠一定是认为,要养好鸽子“亲和力”很重要。这与我们鸽界今天广泛认同的理念完全一致。
他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是对信鸽的定位,他认为信鸽是一种家养动物,是生活在家养状态之下的,这就是信鸽的首要特征。而家养状态与自然野生状态的变异是不同的。
《物种起源》一书导言的最后一句话是:“确信自然选择是变异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中华书局 20112年典藏版《物种起源》 第19页)。那么,另外的途径是什么呢?当然是人为选择。信鸽就是在长期人为选择作用下形成的物种,它非常稳定地遗传了人们想要得到的那些变异特征,比如归巢性强、速度快、在外飞行时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等等。今天我们的赛鸽更是这样,一羽鸽子如果不具备这些品质,那就可以认为它只是一团肉,应该被淘汰于赛鸽这个名称之中。达尔文很赞赏这种人为的定向选择,他说:“我们将觉得人类这种选择力量的伟大,能够使细小的变异逐渐积累起来。”(出处同上)
达尔文在研究中发现在家养状态下,一种性状在一生的某一时期最初出现,往往到了后代亦在相同时期重现,有时稍微提早一点时间罢了。在很多场合,这种性状的定期重现,极其准确。这就给我们今天的赛鸽实践带来指导性的帮助。比如一羽信鸽一到冬季它就比其他鸽子更亢奋、精神和身体状态极好、飞行速度很快,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用它的后代去戴冬赛的特比环或者去主攻冬季赛事。如果成功,则用近亲繁殖的种种方法,就有望把这一特征保存下来,稳定地遗传给后代的后代。新的赛鸽品系可能就因此诞生了。
在家养状态下,一般要经过几代才能够发生大量变异,一旦变异开始,也往往能够继续变异好几代。出现的变异中有的能够遗传,有的不会遗传。各种不遗传的变异,对于我们赛鸽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能够遗传的变异带来的性状差异是无限可能的,人为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对人的有利与否而不是考虑对哪种物种自身有利与否。达尔文研究过,毛腿的鸽子的外趾中间有皮膜;短喙鸽子的足一定小,长喙的鸽子足一定大。这些性状特征都是可以遗传的,但是它们对我们今天赛鸽的影响不大,就可以不去考虑。因为有没有皮膜和足的大小,与我们希望拥有的赛鸽那些优良品质关系不大,既不能加强它们,也不能消弱它们。把握这点之后,再联系两点相关的知识便会得出一个惊人甚至会遭到很多人质疑结论。这两点相关知识是:一、家养动物比野生动物寿命普遍长得多。二、家养动物比野生动物更容易发生变异。那么得出的那个惊人甚至会遭到很多人质疑结论又是什么呢?敬请广大读者关注《关于达尔文对信鸽研究的研究》的第三集。
|